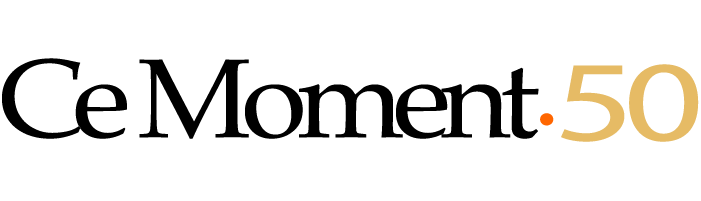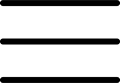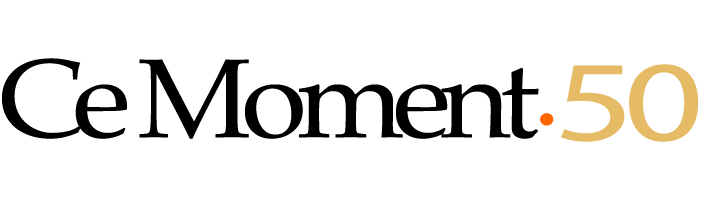上世紀末有一段時間,因工作關係常往返台北與大陸,尤其是北京和上海。那是兩岸尚未直航的年代,早上出門香港轉機,到北京或是上海通常接近傍晚。向來不喜歡飛機餐,在飛機上能不吃就不吃,總想著到達目的地後再說。那也是澱粉還沒成為全民公敵的時代,一碗誠懇的麵總能洗去樸樸風塵,上海的蔥油拌麵、北京的炸醬麵常是最誘人的選擇。那時北京hotel不多,希爾頓靠機場但離市中心太遠不方便,位於長安大街的北京飯店一來位置適中索價合理,二來離榮寶齋不遠,於是經常成為大夥的落腳處。
榮寶齋位於琉璃廠,東西街全長不過四百米,元朝在此設立官窯燒製琉璃瓦得名。東街入口附近有一家叫「一碗居」專賣炸醬麵以及豆汁兒、焦圈兒、芥菜墩等北京庶民小吃的館子,我們常去。石頭台階前幾部黃包車,登上台階舊門楹舊窗框迎人,隨風旌旗飄揚,頗有風弄青簾沽酒市的風情。原以為是和八大居一樣的老字號,後來發現原來是1995年的仿古,跑堂的吆喝聲倒挺道地。炸醬麵經濟實惠,除了醬炸的香,五彩八碟的菜碼才是重頭戲,五塊錢就能飽,也怨不上這擬古的情偽。
都說是老北京炸醬麵,其實炸醬麵源自山東,老北京炸醬麵是在京魯菜館引起的風潮。魯菜到明清兩代已成宮廷御宴的主體,炸醬麵當然只是果腹吃食,上不了席面,是不是魯菜原不值得深究,直到吃過陳先生家home made的炸醬,心裏幾乎可以篤定炸醬山東方是正宗。
陳先生祖籍陝西渭南,娶了煙臺趙小姐,山東陝西都是麵食世界。趙小姐老家煙臺和青島同屬膠東,膠東菜以海鮮聞名,而陳先生的炸醬正是傳自泰山趙克本老先生,除了肉丁還有海鮮入醬。海味的炸醬,比純豬肉丁的炸醬更有層次,很有海風野味的蕭颯。趙先生食譜明載加入乾香菇、金鉤蝦、干貝以及四季豆丁微火烹治,忠實詮釋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純樸,炸乾的香菇金鉤蝦干貝豆角除了提升香氣外,更讓陳家炸醬麵有一種錚錚風骨的爽朗。
小時候住城中區(現中正區),經常去隔壁巷內麵攤打牙祭,記得當時鍾愛麻醬麵,小孩子就圖一個香字,欣賞炸醬麵的滋味是後來的事。當時不喜台灣早期炸醬麵,回想起來可能是因為台灣炸醬少油多水和韓國炸醬麵一樣唏哩呼嚕不結棍兒,少肉多豆乾也滿足不了少年胃口,一直到高中時去學長家吃過「正宗」炸醬麵後才完全改觀。
當年新店中央新村是老國代的歇腳落戶之所,安徽學長有一位北方姥姥,老人家做出來的炸醬當然正宗。陳姥姥說五彩八碟是講究擺派頭,下里巴人沒那麼多花花腸子,當令出什麼就吃啥?中國北方冬天只有大白菜,頂多再加上蘿波切絲當菜碼已經是錦上添花了; 打春就有豆芽、香椿、韭菜; 夏天選擇就多了。
五花肉腴瘦得宜,待鐵鍋燒出一縷青煙後下油,熱鍋冷油下肉丁斷生煸炒,蔥薑末去腥增香,後下黃醬文火咕嘟。醬重於油,因而沈入鍋底而鍋面泛一層油,文火油鍋每冒出一個泡,就一鼻子香,這方才明白這炸字的奧妙。
過去百來年中國動盪,人們無論是自願或是不得已遷徙經常。北方炸醬麵也隨著北方人到處飄泊。客居時經常入鄉隨俗,香港炸醬用辣豆瓣醬番茄醬,台灣炸醬水多油少,但總的來說菜碼明顯不如老北京,而出門在外黃醬也不講究了。
2019年大陸拍了一部戲<<芝麻衚衕>>,老戲骨老套路,算不上頂好。但戲中標誌性的所在沁芳居大量借鏡名醬園六必居,而這六必居可就大有來歷,他們的黃醬從挑黃豆、煮黃豆、磨黃豆、做坯、晾曬、擱鹽、發酵、入缸和封存,無一不講究,這個技法還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肯定。
北京人老話說「井裡蛤蟆醬裡蛆,米裡沙子老規矩」,這講的無非是對衛生與品質的要求。六必居一說是成立於明嘉靖九年,據說金字大匾還是嚴嵩所提,真偽如何並不可考。另外有個風雅的說法,說是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六必居除了不賣茶外其餘皆營銷,因而得名。用六必居的黃醬和甜麵醬各一,取其鹹甜適中溫潤妥貼,私心認為是炸醬的最佳選擇。
台北眷村菜流行好一段時間了,炸醬麵麻醬麵甚至是雙醬麵,是上班族惠而不費的選項之一,唯獨可惜大多沒有菜碼。前些年厲家菜登台,推出仿御膳套餐,其中亦提供鹿尾炸醬麵。鹿尾炸醬興許是舊王孫的作派,畢竟是game meat,非大眾口味,所幸份量不大,權充開眼界開京葷。其實吃炸醬麵無需尋奇便可以充滿儀式感,從和麵擀麵炸醬到準備菜碼,一圍人在白玉般剔透的麵條上添入炸醬(海味尤佳),從碟裝盛著五彩繽紛的台灣蔬菜裡,隨喜揀用,聽著四郎探母,喝著烈酒,時光凝結,像老電影的場景、像林海音的城南舊事,誰說啖時舉箸無風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