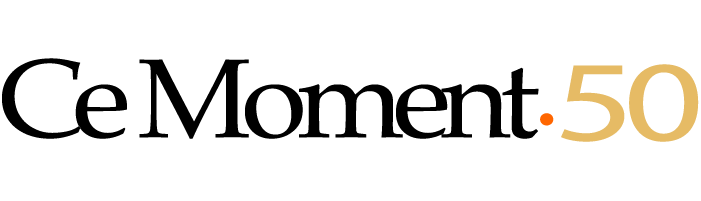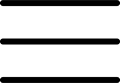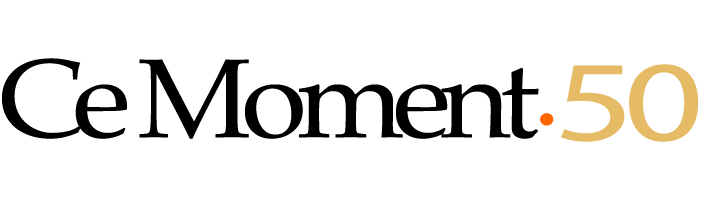大肚山上的校園離台中市區有段距離,是一個讀書嬉戲踱步狂奔的好所在,就是學生人數少,經常讓人有空山靈雨的感覺,迷離惝恍灑脫超逸固然是歷來文青的尋夢作風,但在象牙塔中太久,容易不食人間煙火氣,彼時每隔幾週便得去市區看人。逛街看人之外,打牙祭也是重中之重。牙祭分朔望,囊中羞澀吃碗「小山西」的羊肉麵心裡便美的不得了,月初口袋寬裕,日本料理必定是首選。
妻與我最常去的是座落在民族路的「水車」日本料理,水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可謂是台中日本料理頂級所在,同時期在台北車站希爾頓飯店後頭,也有一家「水車」日本料理,從來沒搞清楚二者之間是否為姊妹店。「水車」和台北開封街的添財在我的飲膳歷程,應該是屬於戰後第二代的日本料理,和第一代的「美觀園」較有「日式」口味。彼時吃日本料理,講究在counter板前お好み任君選擇,食客和師傅相互tango,簡直是做對聯般地相互考驗知識以及味蕾的靈敏度。如果おまかせ是師傅貼的一齣戲碼,お好み便是主人家點的堂會折子戲。舊時講究崑亂不攩,皮黃崑曲任君選擇,或雅或俗各有供俸各取所需,這是自在揮灑的一份教養,お好み正是對師傅的臨場反應。日本料理的流行當然是日本殖民台灣的遺緒,上世紀日本商社駐台的高管不少,但他們吃日本菜的方式相較於台灣富賈的做派,要來得陽春白雪,也妥貼許多。台灣人喜歡喜慶熱鬧,吃日本料理、港式飲茶,經常滿滿一桌,令人疲憊不堪,其實在我看來日本料理,是非常節制的飲食方法,都有一種佗寂平靜的美感,太過就破壞這份寧靜。
日文わびさび佗寂,根據日本美學家大西克禮的說法,是日本人感性的象徵,「佗」隱涵簡單樸素粗糙簡陋的意思,而「寂」則是人觀察「佗」的美的心情。然而簡單樸素是大巧若拙的雅氣並非粗鄙,在高檔日本料理的世界裡,佗寂概念的實踐其實不亞於大西克禮推崇的茶道。日式菜餚基本越高級呈現的越單純甚至會有一絲清貧,譬如品嚐頂級虎豚,薄如蟬翼的河豚刺身,其實非常質樸,即使擺放如菊花也不失孤寂清高之意。喧囂鬧騰固然有繽紛的喜樂,但失去了無語對夕陽的那份清雅安份,品氣就減少許多。
創作者(師傅)的創作主觀性和客戶觀察的普遍本質性之間,在おまかせ的過程裡,兩者之間的權力互動,毋寧是向創作者一方傾斜。客人在規劃設計好的道路,一步一步往前行,即便有曲徑通幽,也是predetermined,這有點類似小朋友聽床邊故事,百聽不厭而可安心入睡,原因無他,無非是結果可以預期,與其說是聽故事,不如說是reconfirmed已知的情節,如此客人便在師傅おまかせ的引導下,逐一驗證。這種吃法,說不上不好,雖然是對師傅信任的表現,但客人的參與度的確被邊緣化。
台灣市場上有些おまかせ的走向令人費解,口味多少在地化略作調整,雖然不是什麼大問題,重點在於度。很多人出國旅遊幾天之後,總得選一家中餐館子整修五臟廟,但很多場景是台灣遊客在抱怨當地的中國菜不道地,然後氣嘟嘟的走出餐館。用同樣的心情來看,過度在地化的日本料理,可能同樣令人失望。壽司醋飯過甜,柑橘皮使用過量,是台灣化おまかせ諂媚當地客人常見的取巧。但是這些都還不是最讓人瞠目結舌的手法,近來飢餓行銷大行其道,為了讓好不容易訂到位子的客人,有一償宿願以及物超所值的感覺,同時也可提高客單價,這些おまかせ像元宵燈會、像國慶煙花般,拼命使用高價食材,整個course火氣十足,完全失去了高檔日本料理應有的婉約。
稍早至交張董事長參加另一位我們都熟識的富商為妙齡紅粉知己過生日,他耐著性子看名店的おまかせ一路放煙火沒多言語,最後師傅端出一個用黑鮪魚中腹為基底,上面刨上滿滿的松露薄片,用超過一百克的魚子醬點綴鮪魚大腹做成的生日蛋糕,最後以金箔裝飾。一整個counter充斥銀鈴般的笑聲和手機鎂光燈肆虐,不顧一個黑鮪魚蛋糕索價兩萬元,只見東家偎紅倚翠滿意極了。張董事長再也忍不住,輕輕吐了一句「沒有人這樣的」,便先行告辭。距事發場景已經過了一個週末,張董告訴我這件事時依然滿心憤慨,可想而知,那浪費不尊重食物,遑論對日本料理這樣非文化遺產的褻瀆,讓他心中有無限的痛心。
這顯然不是おまかせ的罪過,而是店家媚俗、客人審度清雅胸襟侷限之故。上世紀末 かいせきりょうり懷石料理在台灣卻經歷過不一樣的進程。懷石料理從日本茶道演變而來,原是千利休抱暖石對抗飢餓匱乏感的形容,逐漸形成現代懷石料的結構,坊間最澎湃的かいせきりょうり,用「八寸」はっすん領頭,以當令小菜拉開序幕;接著「先附」さきづけ 是真正的開胃小菜,輕盈清新; 「向付」けむこうづ是當旬生魚片; 接著上或魚或肉和蔬菜豆腐為主的煮物「炊き合わせ」たきあわせ; 然後是「蓋物」ふたもの,可能是湯也可能是茶碗蒸; 隨後「焼物」やきもの當季烤魚; 佐以「酢肴」す ざかな清清味蕾; 「冷鉢」ひやし ばち冷碗盛熱主食; 「中豬口」,なか ちょこ)略帶酸氣的湯品; 被酸味喚醒的味覺便可迎接主菜「強肴」しい ざかな以及「御飯」ごはん和醃菜「香物」こう の もの; 最後便是味增湯「止椀」とめ わん還有瓜果甜點「水物」みずもの。
雖然大大小小十四件,經常吃不飽,這種飲食的方法完全呈現わびさび概念,精緻清雅量小的食材,擺置在古雅閑淡的瓷器、陶器或漆器裡,極簡的garnish,用壓縮的空間,表現時間的無限,還有當下的不完美與未完成的永恆美感,如飄落的櫻花。台灣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還有相當正宗的懷石料理,不到十年時間,到處充斥只留其名,貌神不在的懷石料理,甚至有懷石台菜、法式懷石,令人啼笑皆非。
既然おまかせ由質樸無華轉向張揚無度,而かいせきりょうり面目全非,お好み興許是較好的選擇,按照自己的認識與體驗,一個人在板前一貫一貫點,一碟一碟叫,和師傅邊閒聊邊切磋,如此飲膳旅程,和敬清寂遠離塵囂,近年來特別鍾愛。
前兩月到日本出差,圖和辦公室近之故,入住銀座三井飯店。偶而在後巷發現一家自稱能登金澤之幸的小飯館,專門提供北陸漁獲料理,也是おまかせ,但豐儉由人。ふる田老闆是能登半島人,可能因為不諳英文,也可能是個連續受米其林一星肯定之故,表情高傲嚴肅。板前光線昏暗但足夠看他專注料理食物,沒有一絲矯飾,寂得恰到好處,也美味之極,更讓人欣喜的是「十四代」、「大七」等酒造的名酒還可單合選用搭配。一餐典雅おまかせ加上四合清酒,索價不到台北名店三分之一。雖然可以理解每日從築地直飛來的食材矜貴,但一味講究豪奢,卻失去日本料理的神韻。俳聖松尾芭蕉說乾坤之變是風雅之種,飛花落葉仔細觀之聽之,是無止境,自忖這才是消費者參與饗宴的態度吧。